郑州云鹤生态艺术陵园什么时候搬走?
- 2025-10-13
- 编辑:郑州陵园网
清晨的东风渠边,法桐的碎金落在张阿姨的菜篮子上,她刚转过云鹤陵园的入口,就碰到提着豆浆的李姐:“你听说没?咱这陵园要搬了?”豆浆杯上的水珠顺着指缝滴在青石板上,像个小问号。这样的疑问最近在附近小区飘得像柳絮——旁边新建的“枫林逸景”刚交房,地铁12号线“云鹤站”的公示牌立在路口,连卖煎饼的阿婆都在问:“地铁要通了,这陵园会不会挪走?”城市的边界像涨潮的海水,把曾经的“远郊”裹成“内环”,谁都怕身边的老物件突然被浪卷走。
云鹤陵园的门倒不像“要被卷走”的样子。2010年建成时它就主打“生态艺术”,没有阴森的石牌坊,而是两排爬满三角梅的木质廊架,门卫王师傅每天早上给廊下的绿萝浇水:“我刚来的时候这儿是荒草地,现在里面有银杏林、梅园,还有艺术家做的雕塑,上礼拜有对新人来拍婚纱照,说比影楼背景墙有温度。”秋天银杏叶落得像黄金铺地,常有阿姨带孙子捡叶子做手工,连工作人员都说:“好多人把这儿当公园逛。”
搬迁”的准信儿,我查了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官网,《郑州市殡葬设施布局规划(2021-2035年)》里云鹤仍在“现状保留”名单。打电话给民政部门,工作人员明确:“殡葬设施搬迁需符合《郑州市殡葬管理条例》,经多部门论证,目前无申请或规划调整。”社区小王更实在:“真要搬肯定先贴公示,社区大喇叭得喊三天,不会让大家听传言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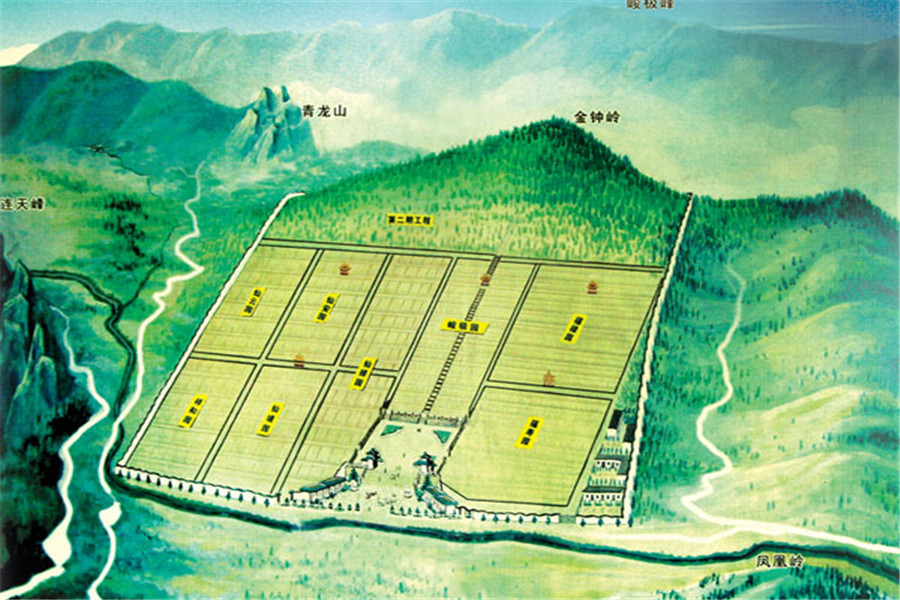
住在附近的人各有心思。刚搬来的小夏皱着眉:“晚上路过有点怕。”住了六年的老周拍胸脯:“我每天晚上去散步,比公园安静,保洁比小区勤快,上次掉钥匙还是保安帮找的。”卖水果的阿强说:“秋天桂花开,我都想挪摊子过去,怕影响祭奠。”每周六来擦墓碑的小吴特意问了陵园:“他们说‘搬’不是说搬就搬,我爸喜欢这儿的银杏,挪了上哪儿找像家的地方?”
傍晚陵园的路灯亮了,暖黄的光洒在“生态纪念园”牌子上。张阿姨和李姐提着煮玉米碰到,李姐说:“问了小王,没这事儿。”张阿姨笑:“没搬好,不然晨练少了歇脚地——里面石凳晒得暖。”风里飘来广场舞音乐,银杏叶沙沙响,有年轻人捧花进来,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,像和亲人说悄悄话。
搬迁”传言更像对城市变化的敏感。我们怕的不是“不变”,是“变”得措手不及。而云鹤的存在,恰好给了敏感一个温柔回应——它不是城市的“补丁”,是和东风渠的水、法桐的叶一起,长成了城市的一部分。就像王师傅说的:“那棵老银杏根扎进渠里了,要搬得连土挖,哪有那么容易?”

- 上一篇
- 下一篇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