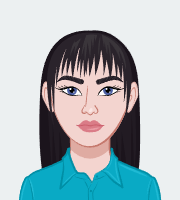云梦山庄在哪里?
- 2025-11-08
- 编辑:郑州陵园网
小时候听外婆说,云梦山庄是个“会躲猫猫”的地方——有人说它在府河的雾里,有人说它在麦田的深处,连地图上都没标过。去年春天我去云梦县采风,特意问了路边卖豌豆黄的阿婆:“您知道云梦山庄在哪里吗?”阿婆用围裙擦了擦手,指着远处的绿浪笑:“顺着府河走,看见那棵老槐树就到了,别着急,风会引你去的。”
我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情往府河走。风把麦田吹成绿色的浪,浪尖上挑着碎金似的阳光,偶尔有白色的蝴蝶斜斜掠过,把影子投在我鞋尖。府河的水很清,清得能看见游鱼的鳞片,岸边的芦苇丛里藏着几只水鸟,扑棱棱飞起来时,惊得水面皱起一层细纹。走了约莫半小时,果然看见那棵老槐树——树干粗得要三个人抱,枝桠像张开的绿伞,树洞里塞着孩子们塞的小石子和祈福的红绳,树底下还摆着个缺角的陶碗,里面盛着半碗清水,应该是过路人给树神的供品。
老槐树后面就是云梦山庄的门。不是想象中雕梁画栋的大门,是两扇旧木门,门环是铜的,磨得发亮,门楣上挂着块木牌,写着“云梦山庄”四个楷体字,字上沾着几点青苔,像刚从旧时光里捞出来的。我轻轻叩了叩门,里面传来脚步声——开门的是个穿藏青布衫的老人,头发白了一半,手里端着个陶壶:“姑娘,进来坐,刚泡了今年的新茶。”

院子里种着两棵桂树,枝桠上还挂着去年的桂花香囊,墙角摆着几盆月季,开得热热闹闹。老人叫周伯,守了这山庄三十年。他搬来竹椅让我坐,倒了杯茶——茶叶是自家种的,叶片卷着,泡开后像展开的绿蝴蝶,茶香味裹着桂香飘过来。“以前这山庄是个私塾,后来没人来读书了,我就留在这里。”周伯摸了摸竹椅的扶手,“有人问我云梦山庄在哪里,我都说在老槐树底下,可其实啊……”他指了指窗外的麦田,“你看风穿过麦田的样子,像不像当年学生们跑着闹着的影子?还有府河的水,夜里会唱催眠曲,唱了几百年。”

我跟着周伯绕着山庄走,厢房的窗户还留着当年的木雕,刻着梅兰竹菊,廊下挂着一串风干的艾草,阳光穿过艾草的缝隙,在地上织出碎金的网。后院有个小池塘,里面养着几只鹅,见人来就伸长脖子叫,周伯笑着扔了把青菜:“这鹅是去年邻居送的,比我还馋。”池塘边的石桌上,摆着半本翻旧的《论语》,页脚卷着,上面有铅笔写的批注——“子曰:贤哉回也”后面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太阳。
傍晚的时候,风里飘来饭香,周伯留我吃晚饭——菜是园子里摘的,空心菜脆生生的,番茄鸡蛋汤飘着葱花,米饭是用土灶煮的,锅巴焦焦的香。我们坐在桂树下吃,天上的云像被揉碎的棉絮,慢慢飘着,远处传来府河的流水声,还有麦田里的虫鸣。“其实很多人来找云梦山庄,不是找一个地方。”周伯夹了一筷子空心菜,“是找一个能慢下来的理由——你看这云,飘得慢,才好看;这茶,泡得慢,才好喝;连日子,过得慢,才有意思。”
那天晚上我住在山庄的厢房,窗户没关,风裹着桂香钻进来,吹得桌上的书页哗哗翻。我望着窗外的月亮——月亮很圆,像块刚烙好的糯米饼,挂在老槐树的枝桠上。远处传来周伯的咳嗽声,接着是陶壶放在石桌上的声音,然后是 silence——不是寂静,是风穿过麦田的声音,是府河流水的声音,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