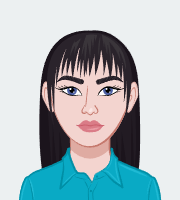郑州云梦山庄墓碑风景图片提供下?
- 2025-10-24
- 编辑:郑州陵园网
清晨的风裹着槐花香钻进衣领时,我正站在云梦山庄的石径上。青石板缝里的青苔连成片,像给石头穿了件浅绿的绒衣,踩上去有点软,像踩在去年的春梦里。风掠过两侧的松柏,发出细碎的响,像谁在轻轻翻一本旧书——书页里夹着槐花瓣,夹着晨露,夹着远处传来的鸟叫。
沿着石径往深处走,墓碑慢慢从松柏间探出头来。不是那种整齐排列的森严,而是像被风景小心藏着的秘密:有的靠在老梧桐树下,树影把刻字筛成碎金;有的藏在一片月季丛后,粉花映得碑身都暖起来;还有的旁边立着棵小银杏,枝桠刚抽新芽,像个踮脚看世界的孩子。最让我停步的是块刻着"爱妻小棠"的碑,碑前摆着个玻璃罐,里面插着几支野菊,花瓣上还沾着晨露——应该是早上有人刚采的,野菊的香混着松脂味,飘得很远。碑身上刻着一行小字:"你说要种满院子的菊,我把它们种在风里了。"风刚好吹过来,野菊晃了晃,像小棠在点头。
中午的太阳爬上松梢时,我坐在石径旁的石凳上歇脚。旁边过来个穿白T恤的年轻人,怀里抱着个小音箱,蹲在不远处的碑前。音箱里飘出轻音乐,是《城南花已开》。他把音箱放在碑座上,又从包里拿出瓶橘子汽水,拧开盖子放在旁边:"妈,我带了你最爱的橘子味。"风把他的T恤吹起来,背后印着个卡通猫——应该是他妈妈生前喜欢的。他蹲在那里,手指轻轻摸着碑上的刻字,嘴里小声说:"上次我带的猫条,楼下的流浪猫都吃了,你说过要养的那只,我已经接回家了,叫小棠,和你名字像吧?"阳光穿过松枝洒在他脸上,他的睫毛上沾着点光,像谁在他眼角放了颗星。

傍晚的风开始变凉时,我往山庄门口走。路过一片银杏林,叶子已经开始泛黄,落在碑座上,像给每块碑都盖了层薄毯。有位老太太坐在银杏树下的石凳上,身边放着个布包,里面装着刚摘的桂花。她看见我,招招手让我过去:"姑娘,吃块桂花糕不?我自己做的。"布包里的桂花糕还热着,甜香混着桂香钻进鼻子。"我家老头子就在那棵银杏树下,"她指着不远处的碑,"当年我们结婚时,就在这棵树下拍的照。现在他躺在这里,每天能看着银杏叶黄了又绿,多好。"她拿起块桂花糕放在碑前,指尖轻轻碰了碰碑身:"老头子,吃块热的,别嫌甜啊。"风掠过银杏叶,发出沙沙的响,像老头子在说"不嫌,不嫌"。
走出山庄时,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,落在门口的玉兰树上。风里还飘着桂香,像谁在说"下次再来啊"。回头望,山庄里的灯光次第亮起来,松枝间的灯串像星星落进了树里。我忽然明白,云梦山庄不是一个只有怀念的地方,是一群人把想念种成了风景——槐香里藏着当年的春,银杏叶里裹着当年的秋,桂花糕里装着当年的甜,每块墓碑都不是冰冷的石头,是带着温度的"记得"。风裹着桂香扑过来,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桂花糕,忽然想,下次再来时,要带瓶橘子汽水,带包猫条,带块热乎的桂花糕——给那些藏在风景里的人,说一句:"我来了,你还好吗?"
- 上一篇
- 下一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