登封公墓一平方多钱?
- 2025-10-27
- 编辑:郑州陵园网
清明前后,登封的墓园门口总飘着淡淡的柏香,来咨询的人攥着折了角的纸,问得最多的就是“这公墓一平方得多少钱?”我见过不少人掏出手机记数字,可往往记了一堆数,还是摸不清头绪——因为公墓的价格从来不是贴在墙上的价签,而是跟“在哪、选啥、要啥”绑在一起的家常事儿。
比如说位置吧,登封的山是活的,好墓园总爱贴着嵩山的余脉。像少林景区旁边的某墓园,沿着盘山公路上去,一抬眼就是层叠的青峦,墓位挨着百年侧柏,风一吹,柏叶沙沙响得像老人的叮咛,这样的“一线山景”,折算到每平方得六七千块;可要是往市区北边再走三公里,离主干道有段羊肠小路的墓园,路边的野菊开得热热闹闹,每平方价格能降到三千出头——不是环境不好,是少了点“抬脚就能到”的便利,却多了份“躲在林子里”的清净。
再说说墓型,这是价格里最“接地气”的部分。隔壁张阿姨选了传统立碑,黑色花岗岩刻着“先母李淑兰”,双穴占了1.3平方,花了五万二,算下来每平方差不多四千;小区的年轻小伙小周选了树葬,就在墓园的银杏林里,只立了个巴掌大的金属牌,连“平方”都算不上,花了八千块——他挠着头说:“我爸生前爱爬嵩山,总说‘死后要当棵树’,这样倒像跟着银杏一起长了。”你看,同样是“葬”,有人要的是“子孙能摸着碑喊妈”,有人要的是“跟着自然走”,价格差得远,可各自都觉得“值当”。
还有服务,别小看那些“看不见”的细节。有的墓园门口有免费摆渡车,清明时有人帮着擦墓碑上的灰,甚至能代祭——去年疫情,我帮李叔联系过代祭,工作人员拍了段视频:摆上他母亲爱吃的枣糕,浇了半杯白酒,连墓碑缝里的狗尾草都拔得干干净净。这样的服务,每平方要多收个几百块,可李叔红着眼眶说:“花得安心,像我自己去了一样。”而有的墓园只卖墓位,后续啥都不管,价格是便宜,可碰到水管漏了、碑刻掉了,得自己扛着工具跑——不是差那点钱,是添堵。

另外还有政策的事儿得提一嘴:登封的公益性公墓只给本地户籍的人用,价格是政府定的“地板价”,每平方两千多,可名额得排队;经营性公墓就没这限制,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在外打工的,只要愿意,都能选——但价格也跟着“活”了,好位置能比公益性的贵两倍。我碰到过老家是周口的大哥,专程来登封买墓,说“父母生前爱来嵩山烧香,葬在这儿,算圆了他们的愿”,哪怕每平方多花两千,他也觉得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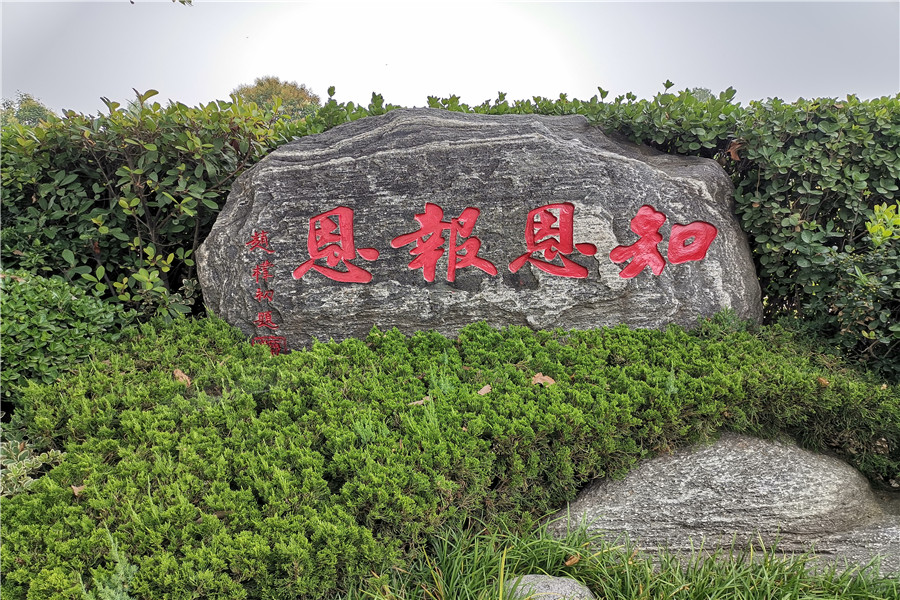
其实啊,我跟墓园的老周聊过,他守了二十年墓,说最心疼的就是“只问一平方价”的人。“你看那对小情侣,选了花葬,把骨灰和着玫瑰花瓣撒在花坛里,没要‘平方’,只留了块写着‘我们一起看春天’的牌子,花了六千块——他们说,这是给爱情留个‘不会老’的地儿。还有那户人家,选了壁葬,就在墓园的长廊里,占了半平方,花了三万,因为老太太生前爱打太极,长廊里每天有老人锻炼,说‘她不会孤单’。”你看,公墓从来不是“买块地”,是给思念找个“能落脚”的地方,价格里藏的是“我懂你”的心意。
昨天碰到之前咨询的王姐,她抱着母亲的照片从墓园出来,说选了离银杏林近的立碑,每平方三千八。她摸着照片上母亲的脸笑:“我妈生前爱捡银杏叶做书签,现在能天天看着银杏落,应该高兴。”风掀起她的衣角,远处的银杏叶飘下来,落在照片上
- 上一篇
- 下一篇


